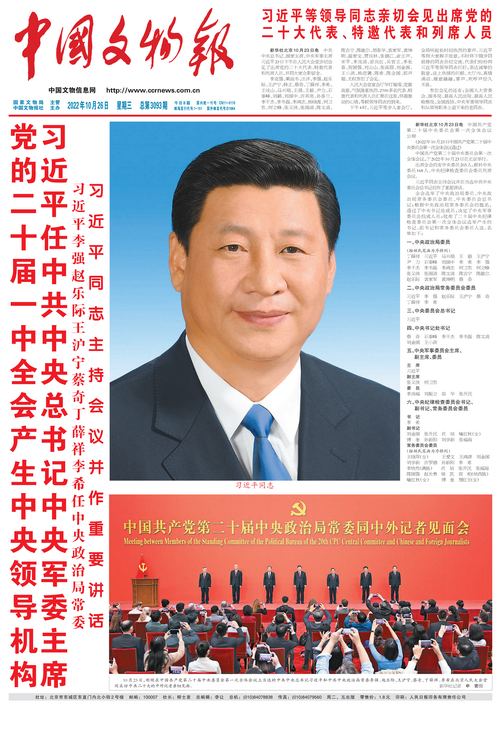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要求,践行“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的“2022北京公众考古季”10月29日在圆明园正觉寺举行了开幕式。本次公众考古季也是北京纪念《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50周年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群,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谈绪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等领导出席活动并致辞。国家文物局考古司、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北京联合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海淀区人民政府等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传承历史文脉,让文物“活”起来
近年来,北京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指示精神,以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为抓手,按照“一轴一城三带两区”总体框架谋篇布局,在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北京中轴线保护等方面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在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国家重大基本建设考古、考古研究机构队伍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持续发力。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群指出,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之际,举行2022年北京公众考古季开幕式非常有意义。迈上新时代新征程,国家文物局将与北京市委市政府携手同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要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将北京考古引向深入,把北京对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贡献讲清楚;要保护传承文脉,让文物“活”起来,以北京中轴线保护为抓手,统筹城市考古和老城保护,为历史文化名城可持续发展提供北京方案;要深化改革创新,打造一流事业发展平台,全面推进文物领域科研管理、人才评价、开放合作政策机制改革创新,奋力开创文物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谈绪祥在致辞中对北京考古工作提出四点希望。一是牢记使命,为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北京贡献,展现中华文化自信自强“新风采”。二是把握机遇,提升考古工作数字化、信息化水平,实现北京考古事业“新发展”。三是广泛动员,发挥高校、文化企业以及行业协会、学会、基金会等社会组织的资源优势,形成共同参与文物保护“新风尚”。四是讲好故事,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展现首都考古成果“新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在致辞中指出,保护文物,利泽万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坚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可信的历史。而考古成果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接下来要继续让考古成果走入群众与社区,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精神文化需求。
发布六大重要考古发现
开幕式上,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名杰发布了一年来北京六大重要考古发现:中轴线、琉璃河遗址、新宫遗址、路县故城、金中都、长城考古。
中轴线考古
南中轴路考古取得阶段性突破,尤其是发现了明嘉靖三十二年(甚或更早)以来依次叠压的七条道路,明确了南中轴路的规制和工程做法,厘清了明清以来南中轴路的历史脉络,揭示了中国自古以来“执中守正”的价值观,是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理念在北京的具体体现。
琉璃河遗址考古
通过考古勘探,在琉璃河遗址的西周燕都城内新发现7处大型夯土水井和数处夯土建筑基础、各时期墓葬138座,城外新发现大面积西周居址。考古发掘出房址3座、墓葬5座,出土铜器、蚌器、骨器、石器、陶器等各类遗物178件。
已提取的青铜器包括鼎、簋、尊、卣、爵等容器,三角援戈、矛、短剑等兵器,成组车马器,人面形饰、组合人面形饰等装饰器。其中,出土于D15M1902号墓葬的尊、卣、爵、觯、鼎内铭文基本一致,铭文内容为:太保墉匽,延匽侯宫,太保赐作册奂贝,用作父辛宝尊彝。庚太保(召公)筑城,证明了燕国与中原的密切联系,彰显了燕国在西周早期时的重要地位。铭文中记载的召公建燕的史实,填补了传世文献中关于西周封国都城建造的空白,明确了西周燕都最早的建城者和建城时间,为北京地区三千年筑城史提供了最早的文献证据。
新宫夏商周聚落遗址考古
丰台区新宫发现夏商周时期聚落遗址,分布面积3万多平方米。遗址由内外双重环壕围合而成,外环壕外东南有墓葬区。外环壕直径约150米,围合面积达1.7万平方米。内外环壕之间分布着大量灰坑。内环壕直径约70米,围合面积约4000平方米。内环壕内发现有房址、灰坑等。房址为半地穴形式,周边有柱洞。灰坑多数为垃圾坑或窖穴,出土少量陶片、动物骨骼等。墓葬区经过有意规划,布局规律,发现早期土坑墓葬22座,墓葬方向一致,基本均为头东脚西,有二层台,多随葬素面折肩鬲、宽沿折腹盆、钵等遗物,有位于头端者,也有位于脚端者。M75为竖穴土坑墓,平面近长方形,直壁平底。木棺东西残长206厘米、南北存宽58~72厘米、残存高30厘米。随葬有玉玦1件、绿松石4粒、陶鬲2件、灰陶罐1件、陶樽2件、陶钵1件。该遗址是一处以大坨头文化(相当于夏代晚期)为主体的环壕聚落,兼有早商和西周时期遗存。文化因素以本地土著文化为主,兼受中原地区和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的影响,尤其M77出土的扣针形带翼喇叭口金耳环,在北京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在国内也极为少见,反映了夏代晚期北京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对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研究提供了重要考古实证。这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该时期带环壕的聚落遗址,对研究早期北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路县故城考古
路县故城南城门遗址发掘面积共1500平方米,清理出城墙夯土基址2处、灰坑13座、道路3条、墓葬2座、瓮棺2座、沟4条、水井3口等。南城门遗址位于路县故城南城墙中部略偏东侧,由门洞、道路和城墙夯土基址等构成。城门中部为西汉时期道路,北朝墓葬、唐代沟渠修建于西汉道路及两侧城墙基址之上,进一步明确了路县故城的使用、废弃历史。
路县故城城郊遗址区南部发掘出两汉时期水井34口、道路3条、沟渠11条、窑址9座、灰坑282座、魏晋时期窖藏1座等。两汉时期的道路遗迹为东西走向,贯穿城郊遗址区南部,宽达7~9米,两侧有附属的沟渠遗迹。两汉道路的发现对了解和认识城郊遗址区的范围与界线十分重要。魏晋时期窖藏主要为一件带盖铁罐,铁罐内有大量铁器、铜器等。该窖藏出土器物共计111件(套),器物种类丰富,基本上以日常生活用具、生产器皿、兵器为主,有少量车马器。这是路县故城遗址首次发掘出的铜器、铁器窖藏,也是北京地区首次考古发现的最大规模的魏晋时期窖藏。东汉水井中发现了木、竹简牍数枚和木印章(穿带印)1枚等。这批木、竹简牍是路县故城遗址、北京地区遗址考古中的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史料价值,对北京地区的考古而言意义重大。制陶遗址区主要由陶窑、窑址与同时期的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灰沟、踩踏面、生土台等遗迹构成。水井可分为土圹井和陶圈井,后者由内外两层陶圈一次性垒建而成,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房址和窖穴有圆形、方形、长方形三种形制,壁面光滑,地面经过人工处理或直接为生土。生土台位于西北,平面呈长方形。陶窑2座、窑址1座为该遗址区的核心遗迹,大体呈东西向排列,相互间隔距离0.40~1.85米。
后屯墓地距离路县故城约800米,发掘古代墓葬千余座,尤以战国墓葬居多,墓主人多为下层贵族和平民。战国墓葬均为竖穴土圹墓。从墓葬排列规律上看,分组明显、排列有序,方向具有一致性,同时期墓葬互相之间基本没有打破关系。推断墓是一处有专人管理、按家族埋葬的公共墓地。前北营墓地位于路县故城东南约1.7千米,共发掘以两汉时期为主的各时期墓葬334座,另有较晚时期的窑址、房址、灰坑等遗迹。西汉墓葬均为竖穴土圹墓,葬具为木棺木椁,或仅有木棺,异穴合葬现象较为常见。随葬陶器以陶鼎、陶罐、陶壶、陶盒为主。新莽至魏晋时期的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圹墓、瓦室墓和砖室墓。其中砖室墓可分为单室、前后双室、多室等。瓦室墓数量较少,均为斜坡墓道单室墓,随葬陶器可见陶壶、陶罐等。城外墓葬区年代从战国至明清时期,各个时期墓葬数量的多寡与城址始建、利用和衰落的时间段基本吻合。
金中都考古
金中都范围内,有牛街和菜园街两处重要发现。
牛街考古发现了丰富的隋唐、辽金、明清时期的遗存,发掘出灰坑、水井、房址、道路、墓葬等遗迹1000余座。灰坑数量最多,约有近1300个。隋唐、辽金时期的灰坑有一部分为窖穴,出土较多陶瓷片。房址、水井和道路的年代大都为辽金时期。房址三十余座,皆为地面式,以单间为主,多间房屋较少。水井8座,分布在房址周围。道路3条,L1、L3为南北向,宽5~6米,长约90米;L2为东西向,宽3~4米,长约60米。这些发现的辽金时期道路、房址等遗迹现象为研究辽南京、金中都城内街巷、里坊布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出土的大量遗物见证了城内居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根据已有考古发现及墓志、石经考证,该区域位于唐代幽州城、辽代南京城、金中都和明清北京城内,为研究北京早期城址变迁提供了新的材料,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具体体现,是展示、实证中华文明史、北京建城史的重要内容。
菜园街发现金代道路、水井、灰坑、灶等遗迹数十处,出土了陶瓷、琉璃、石质、骨质等文物。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的一条金代道路遗迹,东西走向,延伸90余米,最宽处约7米,路土堆积厚度约20厘米,应为金中都富义坊坊内道路,对探讨金中都里坊道路系统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出土的建筑构件及大量陶瓷器,为探讨富义坊内建筑等级和居住人群生活状况提供了基础材料。
长城考古
怀柔箭扣长城遗址发掘面积2530平方米,发掘出5座敌台及敌台间的长城墙体、登城便门、暗门等长城建筑遗址。考古发掘明确了145、144、143三座敌台的建筑规制和工程作法。明确了病害根源和长城建筑营建、倒塌的时序,出土的石碑显示,145号敌台修建于万历十二年,144~143号敌台间长城墙体修建于万历二十五年,一定程度上复原了不同时期长城防御体系的样貌和发展变化。首次在敌台顶部铺房内发现明代火炕、灶址等生活设施遗迹,进一步丰富了长城遗存的文化内涵。发现的刻划棋盘砖、炮台和旗杆墩等,丰富了长城附属设施的类型,提升了对明长城功能和明代戍边生活的认识。
延庆柳沟西山长城遗址发掘面积236平方米。发掘摸清了明代宣府镇南山边垣实心敌台的建筑形制和工程作法,出土的“万历二年题名鼎建碑”,明确了营建时代,证明了长城防御体系由点状防御到连续性防御的发展、演变过程。
延庆大庄科长城遗址考古发掘面积600平方米,发掘出空心敌台2座,登城便门3座,城墙3段。发掘厘清了明代昌镇黄花路长城空心敌台的建筑规制和基础部分的工程作法。首次发现营建空心敌台开凿基槽的实例,也是第一次发现营建敌台前开凿自然山体的实例。该发掘项目还明确了废弃后的坍塌、堆积过程,以及后人对长城的利用过程;明确了空心敌台坍塌过程;明确了城墙地基的工艺作法;明确了长城便门建筑形制;明确了长城上的植被对长城安全的影响;明确了该段长城的营建时代,空心敌台不早于万历二年,墙体建于天启三年、五年前后。
昌平南口城、上关城护城墩遗址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发掘清理墩台6座。发掘首次发现了“半地穴式”铺房遗址,丰富了铺房类建筑的建筑类型,出土的明代早中期瓷片则为寻找明中期乃至早期居庸关关址、复原关城布局提供了线索。
这六处重要发现时代跨度大、分布区域广,完善了北京历史轴线发展的时间链条,进一步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交上了北京答卷。
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时指出,“考古工作要继续重视和加强,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北京公众考古季将深入挖掘首都考古工作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全方位多角度传播历史文化,紧紧围绕“一轴、一城、两园三带、一区一中心”建设,努力做好新时代北京考古工作,擦亮北京历史金名片,真正让文物活起来。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