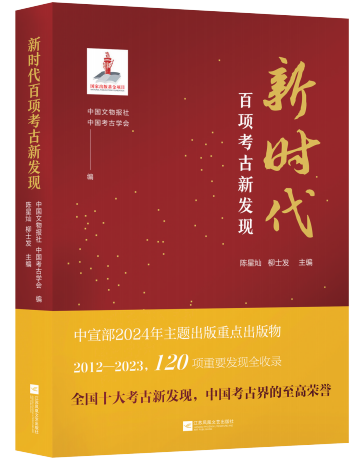
冬日的一缕阳光,暖意融融,好书一本,芬芳四溢。1月9日,由中国文物报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新时代·新考古·新发现——《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新书发布会”在第37届北京图书订货会江苏省团活动区举行。
中国文物报社社长柳士发、副社长赵嘉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张在健出席新书发布会。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北京联合大学校长雷兴山教授受邀参会。本次发布会形式多样、别开生面,亮点频出,既有新书出版背景介绍,又有领导致辞、专家对谈,现场气氛热烈,受到读者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一书收录了2012年至今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全部120个优秀考古项目,并以遗址年代为序编排。该书从考古新发现的角度,记述了新时代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历程。诸多研究成果,都是新时代以来考古学领域的重要突破;很多发掘方法、发掘理念,也充分体现了新时代考古的特征,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诚如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张在健在发布会上致辞所言,文博出版物,应该既能够承载历史的厚重,传递文化的精髓,又能让专业人士的科学阐释以更“接地气”的形式呈现给公众,激发人们对历史文化的向往与热爱。
值得一提的是,《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获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并荣誉入选2024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此外,还入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好书品读月度书榜(2025年1月)。
据柳士发介绍,“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以下简称十大考古)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由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主办,如今已经走过了30多个春秋。作为行业品牌活动,它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一定时段内引领着学科发展方向,塑造着学科内涵的精神特质,以其自身特有的魅力推动着学科大众化的持续深入、以昂扬的姿态劈波斩棘,记录并书写着新时代中国考古取得的成就。
公众着迷、考古升温——时代在变,考古也在变
新时代以来的“十大考古”推介活动,让考古学成功“出圈”,引导公众更关注考古学及相关研究成果。在本次发布会的专家对谈环节,主办方特约新石器、商周研究领域知名考古学者张弛与雷兴山教授参与对谈。从求学到教学,两位学者均亲自主持或参与过多项“十大考古”。谈及新时代以来“十大考古”各项目及其发掘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有何新变化时,张弛直言:“早年的‘十大考古’只有圈内人才会关注。但如今,从初评启动,媒体就会发布相关报道。学术圈外,有一大批文物爱好者每年都关注着该活动,从关注度上来说就跟十几年前大不相同。关注度高了、想了解考古的公众也多了。”
“新时代的十大考古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雷兴山补充道。“第一,必须科学准确,考古从来不是以挖出什么宝贝作为首选价值,而是看工作以什么样的方法进行,是否具有科学的发掘方法,及其科学性和真实性等。第二,需要根据文物、考古遗址的学术价值来重新审视‘十大考古’,更多地关注研究的深度和精度。可以把‘十大考古’看作科研的新进展,也算这些年考古在时代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变化。”
用发现说话 无声胜有声
文物遗存的保护是考古学研究的前提,考古学研究是文化遗产合理利用的学术基础;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工作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缺乏物证的历史是空洞的,缺乏历史的思想是苍白的,“十大考古”发现是我们物证历史的精华,也是我们认识历史的经典标识。
“欧亚大陆的背景下看中国,反之再从古代中国的角度看世界。”以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为例,张弛向读者与观众解释了史前考古发现如何不断地推动着我们的认知。他说道:“皮洛遗址出土的手斧和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度的手斧非常相似。再比如通天洞遗址中发现了五千年前的小麦遗存。我们知道小麦是原产于西亚的,大米和小米原产于中国。那现在我们普遍吃的小麦从何处而来,通天洞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就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和路径。”
上述提到的皮洛遗址入选2021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发现始于配合川藏铁路的考古调查。调查时的偶然发现,加上项目领队带着学术思考和探究的态度,这个项目最终由基建调查转为主动性考古专项调查。新时代的考古工作不断加强课题意识,精细化和规范化程度日益提高。变被动为主动,不再是一味地完成任务、配合基建,而是将课题意识贯穿始终,将配合基建发掘视为解决学术课题的机会,不遗余力将研究做深、做透。
2024年有什么重要考古新发现?这是公众关心的问题之一。雷兴山教授在发布会上透露:“估计看过《封神演义》的朋友,都想知道西岐城是否真实存在?周公、召公、姜太公这三公是不是真的?武王灭商到底带领了多少人?我想告诉大家,2024年的考古发现,就为我们找到了西岐城,它就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的周原遗址。经过几年探索,发掘了三重城墙。通过对城址年代、形制的考察,结合地下出土的陶文,可以完全肯定周原遗址就是灭商以前周人的都城。特别是小城和宫城就是我们考古学家寻找了多年的西岐城。”雷兴山又补充道:“除了陶文外,我们还发现了甲骨文。考古发现的商代甲骨文很多,但西周甲骨文较少。2024年发现的甲骨文中,明确地记载了‘王乎(呼)侯’,更进一步证实了这座遗址和城的性质。”
考古——繁琐且完美
有人说大部分的考古工作都是繁琐的,是经年累月的琐碎工作,是从田野调查到发掘出每一件遗物遗迹,再到慢慢考证、复原古人生活,从而呈现并讲述出考古故事。也有人说考古是一种完美的生活方式,是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完美结合,也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完美结合,既是一项严肃的科研活动,还是一项丰富刺激的探险活动,它的最大魅力在于发现。
考古发现是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正如周原遗址,在同一地点,偶然的机会终于发现城址。这看似偶然,实则是几十年坚持的必然。诚如雷兴山教授所言,考古不是碰运气,只用手铲去挖,而是要用“脑子”挖。
对于大众比较关注的良渚、石峁、三星堆遗址,专家们也交流了最新研究成果。对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三星堆遗址,雷兴山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三星堆几个坑的用途是什么?目前经过考古学界的研究,认为此处原有一座祭坛,祭坛上有神庙,推测神庙内放有青铜器,在不明原因下神庙着火倒塌后将祭器砸碎,于是三星堆先民就挖了几个坑,把青铜器碎片埋在坑底,上铺象牙。其中4号坑和7号坑的青铜器能够拼在一起,说明原来规模较大的文物被很仓促地同时埋在不同的坑里。在我看来,三星堆文化是中原文化在古蜀大地的延续与绽放,是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的结合,两者的发展与平衡展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案例。”
寻未至领域 现不见细微——新时代的考古“新赛道”
新时代以来,各种跨学科新技术在考古学领域应用范围日益广泛。考古科技的发展,让人们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古代遗存,获取关于古人生活的更多信息,通过科学发掘取得的证据,来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进程,以实物证史。由此得到的认识,比历史文献的记载更具体、更广阔、更深入。
“《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书中最后几项涉及水下考古,尤其是南海大陆架的深海考古就是很好的科技考古案例。深海考古需要深潜器,没有技术支撑是不可能发现南海沉船的。此外,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很好地印证了科技能让考古学家看到过去看不到的东西。此前鉴定丝绸主要靠形貌,但如今应用酶联免疫技术就能发现丝绸的残留物质。相信科技赋能会帮助我们发现更多历史的痕迹。”张弛说。
雷兴山形象地把科技考古比喻为考古人的“第三只眼”。他说:“借助科技,我们逐步开展实验室考古,把贵重的文物‘打包’进实验室,从而借助设备更高效更精准地获取更多信息。这种实验室考古也是田野考古的一种延续。将来公众朋友们到博物馆参观,会看到大型玻璃罩里有一群身着白大褂的考古工作人员,那就是实验室考古发掘,也希望我们的实验室考古发掘能够被公众所了解。”雷兴山还透露,未来会有一种更新形式的考古方舱现身发掘现场。“兵马俑刚出土时是彩色的,但与外界空气接触后迅速失去了色彩,这是过去沉痛的教训。在2025年我们会看到一种新的考古方舱,比之前三星堆发掘时使用的方舱技术更先进。在方舱的保护下,文物本身的色彩、性质、出土状态会保存得很完整。大家可以期待并关注大型墓葬的方舱式发掘。”
《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的出版,是向时代抒怀的一种方式,也是承载中国考古发展历程的浪漫篇章。作为中国文物报社与中国考古学会打造的主题出版物,该书以学术讲政治,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大局意识,是在回答时代重大课题中担当媒体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使命的精品图书,是用考古答卷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次实践。
晦涩难懂的考古知识应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走进寻常百姓家,从而启迪一代人的考古梦想,激励一代人的考古追求。这本书将成为搭建在考古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号召广大考古工作者勇于担当、奋发有为,为新时代的考古事业贡献力量。
《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编:中国文物报社 中国考古学会
主编:陈星灿 柳士发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