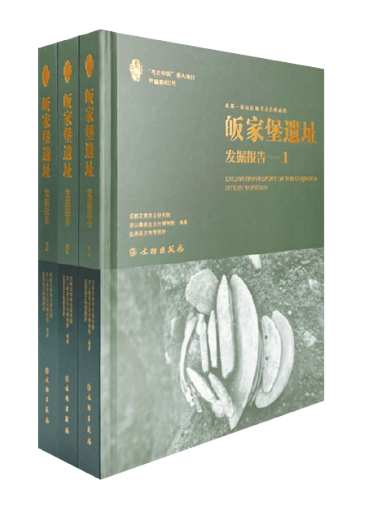
自1926~1927年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组织的中亚考察队在云南省元谋县龙街村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以来,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然而与其他地区星光灿烂的新石器文化相比,金沙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显得黯然失色,以至于学界对其知之甚少。这种情况反映出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都比较薄弱,未能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其根本原因在于金沙江流域迄今为止尚未出版大部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众所周知,田野考古工作是获取考古学研究资料的重要手段,但考古调查或发掘报告未出版就意味着田野考古资料未公布,学界和公众就无法利用这些资料开展相关研究。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面临的正是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其实,经过几代考古人近百年的努力,金沙江流域已发掘了几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为配合向家坝、白鹤滩、乌东德、鲁地拉等大型水电站以及成昆铁路复线等工程建设,云南、四川两地的考古工作者在金沙江两岸发现和发掘了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的就有会理猴子洞、河头地、大坪、河东田、马鞍桥、西昌新庄、羊耳坡、武定长田、江西坟、以鸡嘎、元谋腊甸、丙洪,永胜堆子、枣子坪等十几处,其中河头地、大坪、河东田、马鞍桥、江西坟、长田、腊甸、堆子等遗址的发掘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河头地、大坪、河东田更是超过了20000平方米。然而遗憾的是,这些遗址目前均未出版发掘报告,仅有长田、大坪、河头地、新庄、羊耳坡、枣子坪等为数不多的几处遗址发表了发掘简报。这无疑大大限制了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迄今为止,放眼整个金沙江流域,即便是材料相对丰富、研究相对较多的金沙江中游地区也未构建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序列,对各类遗存的文化面貌及其时代、性质等问题的认识都十分模糊。尽管最新的研究将金沙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分为早晚两个阶段,其中又各自区分出几类遗存或“文化类型”,然而这些遗存或“文化类型”究竟是同一种文化的不同类型,还是不同的文化,它们之间的纵向传承关系和横向交往关系如何,目前也都还不清楚,甚至于对某些遗存是否属于新石器时代都还未取得一致的认识。这种情况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对新发现的遗存的分期与年代、是否属于新石器时代以及属于哪个文化,发掘者似乎不敢做出明确判断。例如,2019年发掘的元谋县腊甸遗址,发掘者认为④~⑦层属于早期文化层,其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未对该遗址的分期以及各期的年代、性质做出明确的判断。从简讯公布的几张器物照片来看,遗址出土的单横耳罐与巧家县小东门、宁南县钟家梁子墓葬出土的同类器完全相同,应当代表了一种青铜时代文化;一些陶片饰绳纹、附加堆纹或以点线纹和光面组成的复合纹饰,与元谋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片相同,明显应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大墩子文化。以单横耳罐、侈口双耳或无耳罐为组合的遗存,在多处遗址和墓地都有发现,应当可以命名为某种考古学文化,譬如可以用最早发现这种遗存的小东门墓地将其命名为“小东门文化”,但迄今学界尚未提出相关命名。关于大墩子文化,目前学界争议较多的是大墩子遗址晚期遗存特别是其中的土坑墓和瓮棺是否属于新石器时代、是否属于大墩子文化。再如会理河头地遗址,发掘简报将该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两组,根据与周边地区出土遗存的比较,将两组的年代分别定为距今3800~4300年、4800~5000年,但对于各组的性质未加判断,只提出第一组遗存与安宁河流域诸多遗址类似,存在交流,第二组遗存与猴子洞、李家坪等遗址出土的早期遗存既有类似又有区别,属于同一类型的文化遗存,至于它们是同一文化的不同类型,还是不同的文化,应当如何命名,都没有明确的意见。
以上问题都凸显了出版一部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对于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来说,《皈家堡遗址发掘报告》的出版无疑是一座里程碑。其重要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为确认金沙江流域其他遗址出土新石器遗存的性质和年代树立了一个可靠的标尺。金沙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虽然已有“大墩子文化”“白羊村类型”“闸心场类型”“横栏山文化”等命名,但或因资料较少,或因出土资料含混而未能准确把握文化面貌,或被新发现的资料证实为青铜时代遗存,都难以作为比较的标尺。皈家堡遗址经过4次发掘和1次试掘,揭露面积2500余平方米,新石器时代堆积包含②层至最底层的原生堆积以及房址24座、灰坑183个、灰沟5条、器物坑4个、墓葬15座、特殊遗迹20个,遗迹类型多样、数量较多,出土遗物特别是陶器十分丰富。报告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两期,第二期又进一步分为四段。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报告公布了141例碳十四测年样品的测定结果,出自新石器时代单位的就有108个(不包括4例无法满足实验需要的样品)。一个遗址短期集中发表数量如此之大的新石器时代碳十四测年数据,放眼全国都是十分罕见的,就连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历经30余年(1974~2006年)也才测定了78例样品。除了数量多之外,发掘者还特别注意系列样品的采集要求,采样单位不仅涵盖了各个年度不同发掘区的每一层和绝大部分遗迹,并且大部分单位都测定了2个以上的样品。高精度系列样品方法保证了皈家堡遗址所测数据的高质量和可靠性。皈家堡出土的两期新石器时代遗存在目前已发表的、各自所代表的同类或近似的遗存中都是最丰富的,文化面貌均比较清楚,文化性质不同,其早晚关系既有层位学证据,又有测年数据支撑,为金沙江流域特别是中游地区其他遗址出土新石器遗存性质和年代的判断提供了可靠的比较材料。
第二,为金沙江流域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提供了一个样板。皈家堡遗址于2015年试掘,2016~2019年四次发掘,距发掘工作结束仅时隔5年就出版了3卷本考古发掘报告,在考古报告普遍积压、欠账的今天,这种速度是十分罕见并且难能可贵的。尤其值得称赞的是,报告编写者并没有因为整理资料、出版报告的时间短促而在编写质量上有所妥协。报告虽然采用的是按单位发表遗物的方式,但对出土遗物也进行了全面的类型学分析。报告附录还公布了动物遗存、植物大遗存、微体植物遗存研究报告,为研究者提供了该遗址的全方位信息。
系统、全面、准确、客观地公布田野考古工作所获资料,是考古报告所担负的基本使命。就此而言,《皈家堡遗址发掘报告》不但完成了这一使命,并且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研究,堪称优秀。不过,任何一部考古发掘报告都不是完美无瑕的,《皈家堡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报告未明确两期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性质。报告仅指出第一期与猴子洞早期遗存、李家坪早期遗存、河头地早期遗存、堆子遗址第一期、银梭岛遗址第一期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第二期与枣子坪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堆子遗址第二期遗存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然而除了枣子坪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被发掘者认为属于白羊村文化外,其余几处遗址的发掘者均未对各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性质做出明确的认定或提出文化命名。其实,皈家堡遗址的发掘者曾撰文将第二期遗存命名为“皈家堡文化类型”,认为其与“大墩子文化类型”“白羊村文化类型”“新光文化类型”“横栏山文化类型”共同构成了“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发掘者显然已经注意到皈家堡第二期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或类型,但报告未就这方面的认识展开讨论,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第二,报告将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两期,第二期又进一步区分为四段,各期各段仅列举了若干代表性单位,未涵盖新石器时代全部遗迹,并且在遗迹登记表中新石器时代遗迹的时代全部登记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没有具体到期段。此外,测年数据登记表也未注明样品出土单位的时代,不少单位没有被列入报告所分各期段,研究者需要逐一确认各单位的时代和期段,使用起来颇为不便。
第三,动物遗存只提供了研究认识,而未公布各单位出土动物骨骼的鉴定结果。就该遗址新石器时代动物遗存而言,动物遗存研究报告提供的是新石器时代先民开发与利用动物状况的认识,对于该遗址两期五段、时间跨度长达13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来说,这一认识显得十分笼统。此外,该遗址两期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性质并不相同,其他研究者无法根据这一研究进一步了解每一期所属考古学文化的动物开发与利用状况。
尽管报告存在一些瑕疵,但瑕不掩瑜,作为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部大部头考古发掘报告,《皈家堡遗址发掘报告》以其全面、丰富的资料和可靠的分期与年代标尺,必将引领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迈入新时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明进程研究”(项目批准号24XKG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皈家堡遗址发掘报告》(全三册)
编著: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