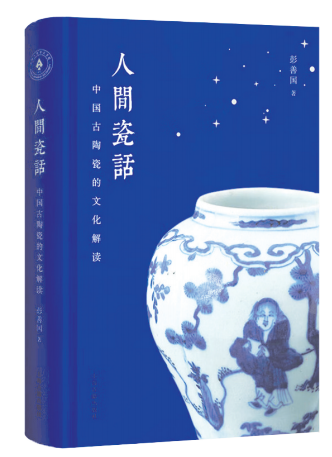
瓷器是古代中国的伟大发明之一。不过,古人似乎并没有把这项发明太当回事儿,他们留下的文字记载,和瓷器相关的可真不多——胼手胝足的制瓷工匠没功夫记录它,文人墨客没兴趣记录它——以至于瓷器出现的时间等陶瓷史上的重大问题,往往要靠考古工作者依据出土文物来解决。
记载的稀少,使得存世文献愈加可贵;记载的片麟半爪,又给了后人的解读以相当模糊的空间。大文豪苏东坡的《试院煎茶》诗,记了一句“定州花瓷琢红玉”,留下一桩陶瓷史的公案:到底是定窑白瓷呢,红瓷呢,还是可作别的解读呢?又比如,北宋晚期享誉禅林的诗僧惠洪,在他的一首诗中说“点茶三昧须饶汝”,今人有把“饶汝”解释为景德镇瓷器和汝窑瓷器的。这是文本的误读,还是北宋汝瓷文献的新发现呢?与后周世宗柴荣联系在一起的谜一样的柴窑,是否会有在开封的蛛丝马迹呢?
“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是广为传颂的名作。词句中“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的玉枕,经常被指为景德镇窑烧造的青白瓷枕。其实宋代既有真正的玉质枕头,烧造瓷枕的窑场也不止景德镇一处——说不定易安居士的枕头,是“巩人作枕坚且青”的“碧瓷枕”呢。说《醉花阴》里的枕头就是青白瓷,大概是视一般为特殊,把宋人的文学化描述,当作了具体的事物。
长沙窑的高温釉上彩瓷,是唐代瓷器装饰的一朵奇葩,它上面的花花草草,唐人有没有记录过呢?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诗中写到“湘瓷泛轻花”,既有湘瓷又有花,不由得让人把它和长沙窑彩瓷作联系。然而在唐人语境里,“轻花”是指煎茶时茶汤表面的浮沫——飘飘然像轻盈的枣花一样,故云轻花——它和瓷器的花纹风马牛不相及。
当然,古人关于瓷器的记载,有不少还是相当明确而靠谱的。司马光在叠石溪的瓷窑畔购买别墅,他的好友范镇作诗描绘瓷窑生产的场景,“累墙瓷隐辚”“钧盘疾甚车”等句,生动再现了北宋熙宁年间河南宜阳窑的窑业盛况。南宋刘学箕雅好盆栽石菖蒲,他所使用的“鄱阳白瓷方斛”,则是时人称呼景德镇产品为“白瓷”的一个证据。
陶瓷器的功能总是与时俱进,不断拓展。普通饮食盛贮之外,可作文具,可演奏音乐,可用来焚香祷祝,不一而足,甚至还可以拿来作储钱罐。考古学家从唐洛阳城履道坊白居易的宅第,发掘出土了几方陶瓷砚台,他们认为这是香山居士翰墨生涯的写照。然而根据考古类型学编年,白居易宅出土的圆形多足辟雍砚,在8世纪初即退出历史舞台,远早于白居易(772-846年)生活的年代。可见拿名人来比附具体的文物,还需要慎重地辩证。陶瓷乐器中最有名的当属腰鼓,名相宋璟就很擅长演奏河南鲁山窑烧造的花瓷腰鼓,他还和唐玄宗交流过鼓艺。击瓯的技艺,被写进唐人传奇,其声音被温庭筠赞誉为“碎佩丛铃满烟雨”,似“惊沙叫雁、高柳鸣蝉”。不过,邢窑、越窑似乎并不专门生产用来“击瓯”的瓷器,我们也很难从出土文物中把它们甄别出来,因为这只是饮食器具功能的巧妙转换,而非创造出一种新的乐器。
在中晚唐长沙窑的一件执壶上,制作它的工匠,忽然心血来潮,用铁彩写下“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四句话。打这时开始,瓷器就从实用的坛坛罐罐,升华为人们可以之寄寓情思的道具。当元代景德镇的窑工,在青白瓷器上用釉里红书写“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的句子时,我们真要感佩他们对文学典故的认知水平。当我们看到瓷器上的寒山、拾得从禅门散圣,到明清时期沦为祝寿祈福的角色,不禁会感叹世俗改变神祇的力量。康熙时期“青云居玩”主人绘制青花笔筒上的《霞笺记》场景之前,一定读过或看过这部戏曲,如同“红叶传媒”的美好寄托一样,吸引他的肯定不是戏曲所本的明代传奇《心坚金石传》中动人心魄的悲剧,而是该曲汇人生四大乐事于一身的大团圆结局。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人间瓷话——中国古陶瓷的文化解读》
作者:彭善国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