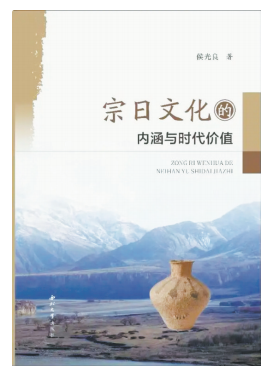
侯光良教授的新作《宗日文化的内涵与时代价值》(以下简称《宗日文化》)一气读完,意犹未尽。把一个谜一般的史前遗址和文化写得如此机杼别出、条理清晰和通俗生动,作为宗日遗址考古发掘者的我是做不到的。因为考古学家都是把自己当作仓库管理员的模式来训练的,我们只会将考古当作器物而不是人物来对待。
宗日遗址是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90年代青海省文物处考古队做了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9800平方米;21世纪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河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又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再加上羊曲遗址因修建大坝而进行的近30000平方米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可以说宗日遗址和宗日文化是青海省迄今为止的发掘项目中发掘时间最长,发掘面积最大的考古遗址和考古学文化。虽然宗日遗址和宗日文化的田野考古工作已经做得很多,但室内整理和相关研究却远远跟不上,因为宗日文化的发现时间毕竟太短,学术研究的积累还太薄弱。在这样一个考古的学术背景下,《宗日文化》就显得很有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了。初读之后,有以下几点感受,权当此书的推介:
迎难而上,解决学术前沿问题
宗日遗址于20世纪90年代发掘后一经披露,便惊艳了世人和学术界。对于世人来说,是宗日遗址出土的舞蹈盆和二人抬物盆,这成了青海省古文化和文物旅游的标志;对于学术界而言,则是出土的与仰韶和马家窑彩陶体系迥然不同的宗日陶器。青海境内的马家窑文化是我国史前彩陶文化中研究比较早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之一,从最早1923年安特生在西宁、贵德等地发掘和认识马家窑文化开始,接着被如高本汉、阿尔纳、亨策、瓦西里耶夫等外国学者严重关注过和讨论过,后又经夏鼐给马家窑文化定名,到石兴邦和严文明、谢端琚等人进行马家窑文化来源以及分期研究等,对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的认识与研究应该说是比较充分的了。而就在这种充分认识的情况下却又出现了学者们根本不认识的宗日文化,这让考古学家们感到很挫折和沮丧。
宗日文化是新发现,要解决的却是旧问题,即马家窑文化的适应与进化。新的文化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来源问题。对于某一考古学文化的来源追踪一般有两种理论:当地起源论和传播论。发掘者陈洪海对宗日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之后认为,马家窑文化传播到共和盆地,然后主要是因为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原因,结合当地的细石器狩猎文化而变异成宗日文化,正如同仰韶文化进入到甘青地区变异成马家窑文化一样。在这里,陈洪海将当地起源论和传播论融合在一起了。《宗日文化》采用了陈洪海的说法,还列举了沙隆卡遗址剖面的第17层细石器文化层中发现有陶片(距今7.8~7.7千年)、在江西沟2号出土的距今6.5千年前后的陶片、下大武2号地层剖面发现的距今6.2千年前后的夹砂陶片等作为证据,用细石器技术社会中使用陶器的考古发现,来证明马家窑彩陶文化与细石器狩猎文化相遇后所产生宗日陶器的可能性——代表农业的陶器与代表狩猎的细石器之间的结合是有先例和传统的。考古学跟破案一样,只讲证据,不重推理。所以《宗日文化》中这看似可有可无的一段举例描写,却凸显出考古学这一学科的科学性。
《宗日文化》中将细石器称为“细石器文化”,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合乎中国考古习惯的称呼,在中国考古界习惯上更多称之为“细石器技术”。但在国际上,譬如在印巴次大陆,细石器是可以称作“细石器文化”的。
线条清晰,教科书般条理
按传统的说法是“功夫在诗外”,按现在的说法是“你要写青海,就不能只写青海”。在这里就不能光写宗日遗址,你要写与宗日相关的其他文化,说清宗日文化的来龙去脉。宗日文化是分布在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所以黄河上游的水系和水资源、植被和土壤、泥沙、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环境、文物保护单位的时代与数量、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关的重要遗址统统被用图表和数据的形式清晰地加以展示,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方位并数据准确的关于黄河的背景知识。
然后,《宗日文化》随即围绕着青海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从考古学文化的堆积、年代学、植物、动物、文化的区域分布等方面系统加以介绍,逻辑叙述细石器狩猎文化何以发展成马家窑和宗日以农业为主的考古学文化,将发掘者陈洪海的专精研究集中并通俗化,从马家窑和宗日两种陶器在各期所占比例、从仰身直肢葬和俯身直肢葬的分布情况,从食物结构,也就是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结果所显示的两组葬式的宗日人群在食谱上的早期差别等等,用多学科研究的具体数据来说明宗日文化是如何适应当地环境并得以进化的。从黄河收缩到黄河上游,再集中到青海的共和盆地、河湟谷地,最后聚焦在宗日遗址,由大到小、由古及今、由细石器狩猎文化到新石器农业定居,层次分明,逻辑清晰,教科书般的逐次递进。
角度新颖,写人而不仅仅是写物
要将一个考古遗址写成一部书,传统考古学家的做法是对物不对人,也就是发掘报告。要对人的话,在考古界叫“透物见人”,是考古的一种境界和目的之一。21世纪以来,过程考古学成为时代主流,多学科的研究手段才能使考古学家“透物见人”。
侯光良教授的专业是第四纪地理环境与人类,所以他对环境考古自然是轻车熟路。这种轻车熟路首先表现在全新世以来青藏高原地理环境与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对应和相互关系上,这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人地关系。以羊曲遗址为例,《宗日文化》通过非常细致和精确的不同区域的大量孢粉分析数据,从而指出“盆地云杉基本消失,盆地内生长着以藜科、蒿属和禾本科为主的荒漠草原,达连海周围开始发育以莎草科为主的沼泽草甸。总的来说,该时期森林在缩小,荒漠草原在扩大,说明环境已向凉干方向发展……进入全新世以来以草原植被为主,植被覆盖率较高,适宜野生动植物生存,也成为史前人类频繁活动和定居的理想区域,为高原细石器采集狩猎人群和低海拔河谷农业种植人群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必要条件。”这样便使考古学家通过环境和气候的分析对两种经济形态下考古学文化发生碰撞的情形有了更有科学依据的论述。遗址区炭屑浓度对人类活动具有很好的指示意义,人类活动强对应的文化层用火频率高、强度大,炭屑浓度高,人类活动弱对应的文化层用火频率低,强度小,炭屑浓度低。在羊曲遗址南坎沿自然剖面对沉积物做光释光和炭屑分析中显示,其中距今6.7千年时达到整个剖面浓度最大值;距今4.7千年后炭屑浓度介于1770~15500粒/克之间,浓度再次升高,在距今3.8千年处浓度较大。这些数据与细石器层位、宗日文化层位以及齐家文化层位相对应,从而有助于考古学家对相应时段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的分析研究。多学科的介入,使考古学家走出器物学研究的困境,进入对古代人类及其社会和生活状况进行分析的领域。
图表生动,数据一目了然
大量精美图表的使用,这不仅仅是《宗日文化》一书的亮点,同时也是侯光良教授的一贯特色。图表的优点在其直观性、数据性、精确性,或者一句话,即科学性。纵观以图书版面为特征的国际考古出版物(主要指以英语为载体的),会发现大致可以分作三个阶段:插图阶段、图表阶段和文表阶段。考古以图为主,没有图就无法进行考古学研究,所以早期考古学书籍都配有大量的手绘图。从过程考古学,尤其是20世纪最后的20年以来,手绘图数量大大减少,被很多表格所代替。因为新考古学(亦即过程考古学)号称是科学考古学,图表所具有的数据化和精确化便是“科学性”的表征之一。从21世纪以来,在越来越多的考古学研究中,手绘图越来越多地被照片或电脑分析图表所代替,表格(包括各种各样电子图表)几乎一统天下。这种变化趋势似乎被学术界认为是“科学化”的发展趋势,我之所以在这里将科学化打上引号,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这么认为。无论学者们怎么认识,但这种变化和趋势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学术与时装一样,也有流行和时尚的区分。
传统考古学家的训练包括自己制作遗迹和遗物图,但要运用电脑软件制作地图和分布图,以及电脑分析图表,则是新考古学的要求。对于一般人而言,自己制作一幅图并非易事,往往直接拷贝或请人帮忙,但电脑分析图表,则是非亲自为之而不能的事。所以考古界有一种不成文的默契认识,一个作者是否为专业考古学家往往是通过图来判断的。也许因为侯光良是地理系的教授,所以文中还有大量的地图、分布图等,这也是《宗日遗址》的闪光点,比如“黄河流域各时期文保单位的核密度状况”中的几幅文物点分布图,使我们直观、准确和一目了然地得知文物在不同时期的分布状况。
此外,《宗日文化》一书中还灵活运用小贴士对一些专业的却非叙述主题的知识和概念加以解释,不仅有助于对整个行文的理解,而且灵动了版面,活跃了叙述的沉闷。
(作者单位: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宗日文化的内涵与时代价值》
作者:侯光良
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